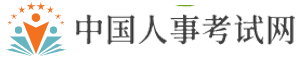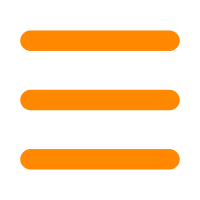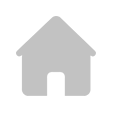刑讯逼供之所以产生,我以为和法律规范、认识观念有非常大关系。
1、法律规范方面。
(一)“如实回答”义务的不合理。
国内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职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这句话明确规定了犯罪嫌疑人有“如实回答”的义务,同时也意味着他们假如不“如实回答”的话,就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但“如实回答”的首要条件是犯罪嫌疑人开口说话,怎么样才能使其开口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即便犯罪嫌疑人对侦查职员的问话予以回答,也面临着其回答是不是“如实”的问题。假如侦查职员觉得其没回答或者其回答并不“如实”,没尽到“如实回答”的义务,那样就意味着其需要承担不尽义务的责任,并遭到相应的惩罚。
然而对此我却有几个方面疑问:“如实回答”的合法性大家姑且不论(在1966年12月16日,第21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其中第14条就规定“其他人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一个人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1998年十月5日,国内签署加入了该公约,然而国内刑事诉讼法目前却依旧规定了“如实回答”的义务),就是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犯罪嫌疑人假如尽到“如实回答”义务,那样他就应该获得相应的权利,但犯罪嫌疑人有什么权利法律并没规定。除此之外,义务与惩罚也是相联系的,不履行义务,就需要进行惩罚,不然就是对其他履行义务个人的不公正,但这种惩罚是什么?是否就意味着可以进行刑讯逼供呢?国内现在并没规定。而英美法系和国内法系绝大部分国家因为确立了“沉默权”规范,被告有权维持沉默,口供与定案失去了势必联系,刑讯逼供也就大大降低了。
(二)侦查活动未受监督。
依据国内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侦查机关除去有侦查取证的职责外,还有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手段的权力,这使得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客观上处于一种严密控制的不公开情形之下。这个时候,不只犯罪嫌疑人的亲属、律师没办法与其见上一面,就是负有检察职能的检察机关也没办法对此进行监督。所以,犯罪嫌疑人是不是过去遭到过刑讯逼供,外人根本无从而知。而遭到刑讯逼供的犯罪嫌疑人即便在法庭上以曾遭到刑讯当场翻供,他也非常难提出证据加以证明。审判机关最后还是以证据不足为理由,认定犯罪嫌疑人在侦查机关曾做的供述是合法有效的(尽管事实上并不这样),从而做出不利于犯罪嫌疑人的判决。这客观上为刑讯逼供的发生提供了有利条件。我觉得国内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有关规范,将关押犯罪嫌疑人与提审分为两个不一样的部门,犯罪嫌疑人一旦从关押场合被提走,即开始全程录音、录像,在时间上不能有间断。该录音、录像资料一式两份,并交给犯罪嫌疑人一份留存。或者确立律师介入规范,规定讯问犯罪嫌疑人时需要有律师在场,如律师不在场,则所获得的口供视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三)证据规范的不健全。
由于口供具备获得容易、证明价值高等特征,故而其深得侦查职员的“喜欢”。但这种对口供的偏爱,不但会鼓励和怂恿刑讯逼供行为的产生,更紧急的是,它会使侦查职员产生工作惰性,办案时过分重视口供。
[1][2]下一页